賈米爾·吉瓦尼(Jamil Jivani)講述了他在北美和中東地區擔任青年活動家的經歷,在西方的ISIS新兵、幫派分子和新納粹分子之間取得了驚人的相似之處。
在他的家鄉多倫多,吉瓦尼勉強逃脫了犯罪和幫派暴力的潰折,他畢生致力於幫助其他處於危險中的年輕人在北美各地的城市中避免這種命運。2016年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他前往歐洲和中東,協助發展穆斯林社區的社會服務機構Community Outreach Group,專注於阻止ISIS的招募。
《年輕人為何憤怒》講述了吉瓦尼作為一名社運人士,在當今最危險和最棘手的問題之一的前線的故事:世界各地憤怒的年輕人中暴力的爆炸式增長。吉瓦尼講述了他的個人故事,並描述了他進入社區外展運動,他與北美被剝奪公民權的有色人種,以及中東和非洲處於危險中的青年的合作,以及他與白人工人階級的經歷。讀者與他一起學習,因為他介紹了各種各樣的年輕人,並採訪了那些試圖幫助他們的人,在這些群體之間畫出相似之處,駁斥了人們普遍認為他們彼此截然不同的信念,並提供了對抗這一全球趨勢的具體步驟。
以下內容摘自《年輕人為何憤怒》
社會對我的歧視以及父親的缺席,我不知道應該成為什麼樣的男人。《年輕人為何憤怒》
巴黎恐怖攻擊
父親的缺席對於男性的影響
有害的男性氣質
他人看法如何傷害個人對自己的感受
青少年輔導員的重要性
工作能降低犯罪機率
後記
巴黎恐怖攻擊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國巴黎及近郊發生了一連串自殺爆炸和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近五百人死傷。這些暴行是由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九名男子所執行。法國總統稱巴黎襲擊是針對法國的「戰爭行動」。
在接下來的幾天,新聞名嘴和在社群中帶風向的網友迅速聚集在他們的意識形態陣營中,把攻擊者視為某個宗教或種族的無名代表。一方把殺戮歸咎於宗教和文化,而另一方則認為恐怖行動肇因於種族主義。
巴黎恐攻的兩名主謀阿布德哈米.阿布阿烏德(Abdelhamid Abaaoud)和薩拉赫.阿布德斯蘭(Salah Abdeslam)在宣誓效忠ISIS之前,雖然生活和一般人並不一樣,但卻未必顯示他們日後會成為殺手。兩人均於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在比利時出生,父母是第一代摩洛哥移民。他們在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一起長大。兩人都犯過一些輕罪:二〇一〇年,他們倆因擅闖一個停車場而同時被捕。阿布阿烏德至少入獄三次,而阿布德斯蘭則嘗試創業:他在莫倫貝克和人合開酒吧,也兼任經理。兩個人的背景都並沒有顯示他們對伊斯蘭教信仰特別虔誠或傳統。父母親的宗教和文化在他們的生活中,似乎遙不可及。
令我驚訝的是,巴黎恐襲者與我在多倫多郊區長大時相處的一些年輕人有相似之處:他們都是移民的孩子,生活在弱勢社區,犯過一些小罪,並且雄心勃勃。當然,我的同輩中並沒有人由輕罪演進為恐怖主義極端分子,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同樣容易受到破壞性的影響。在成長期間,他們經常禁不起身邊的人遊說,做出壞事。他們惹上諸如打架之類的麻煩,都是因為周遭有人鼓勵他們犯罪的結果。
父親的缺席對於男性的影響

「回顧我的人生,我可以看出在哪些地方父親的干預或正面的榜樣可能阻止我做出錯誤的選擇。比如我高中時經常打架,主要是因為我認為男子氣概就是要衝突。我以為要做男人,就要打鬥。」
承認父親的重要並不是否認母親在年輕男性的人生中不重要,而是承認男性的角色模範攸關緊要,如果他們缺席會造成重大的後果。非營利組織全美父職推動協會(Natinoal Fatherhood Initiative,NFI)致力於終結父親缺席的情況,它宣稱:「今天美國面臨的種種弊病,幾乎都有父親因素。」(這個大膽的說法得到了研究的支持:研究顯示,沒有父親的孩子較容易出現行為問題,過貧困的生活,遭受虐待或忽視,嗑藥或酗酒,在學校常會留級,未成年生子,以及去坐牢。NFI的研究還顯示,父親缺席的青春期男孩特別容易犯罪,或做出其他違法行為。
普林斯頓大學、康乃爾大學和柏克萊加大的研究人員在二〇一三年做的文獻探討也發現,缺乏父親的情況對孩子會造成嚴重的影響。這些研究人員探討了四十七份來自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研究,結論是:「我們發現有力的證據,顯示父親缺席會對孩子的社交情感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尤其會讓他們增加外在化行為(例如攻擊挑釁和尋求注意)。如果父親缺席的情況發生在童年初期,這些影響可能會比發生在童年中期更明顯,而且對男孩比對女孩更明顯。」
擔任《性別與父母身分:生物和社會科學觀點》(Gender and Parenthood:Bi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tific Perspectives)共同主編的維吉尼亞大學布萊福德·威爾考克斯教授(W.Bradford Wilcox)概述了父親為孩子的生活做出貢獻的四種獨特方式:(1)在與孩子玩耍時,示範如何適當運用身體而非暴力; (2)鼓勵兒童冒險和獨立; (3)提供身體保護或身體保護的外觀;以及 (4) 提供嚴格的紀律。威爾考克斯認為,如果沒有父親提供這些貢獻,兒子「更容易在青春期和成年初期被襲捲入狂飆動盪之中。」
有害的男性氣質

談論年輕男性的經歷和他們面臨的挑戰並非總是很容易。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遇到了來自多方面的阻力。
在年輕男性自己這方面,他們通常厭惡表達自己的感受,也不願分享自己的奮鬥經歷。在我的人生和工作中,這一直是主要的課題。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八歲時,我的父親情緒失控,在我床邊哭泣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父親NOW」的金恩·皮凱茲描述自己戴著面具,為什麼我在十幾歲的時候上網尋找榜樣。
《進階護理雜誌》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上有一篇評論點明了一些趨勢,顯示男性對男性氣概的看法對他們求助的意願產生莫大的影響,即使他們生病亦然。男性崇尚陽剛之氣,排斥缺點或軟弱,因此男性較不願意尋求幫助。「事實上,國際男性健康論述中常見的理論主張:男性不得表現出疾病或『沒出息』,因為傳統男子氣概的想法或社會指定的男性角色總認為軟弱無助的男性沒有陽剛之氣。」
《沙龍》(Salon)雜誌的阿曼達·馬可特(Amanda Marcotte)曾寫過一些文章,談到有些男性使人難以公開談論男性氣概,尤其是「有害的男性氣質」,她對「有害的男性氣質」定義為「一種特定的男子氣概模型,以支配和控制為重。」她說,每當她談起「有害的男性氣質」,就總會碰上「抱怨不停的哥們,他們會立刻認定或假裝認定:女權主義者是在聲討所有的男性氣概,儘管『有害』一詞意味著某些形式的男性氣概無害。」
有的人也把與男性氣概相關的討論認為是攻擊女性和女權主義,因此排斥這個話題。在西方國家,自古以來男性身分認同一直都排斥女性,並賦予男性特權和利益,因此男性獲得「心理工資」 (psychological wage)之利。W.E.B.杜波伊斯創造了「公共和心理工資」一詞來描述十九世紀後期美國白人勞工超越黑人勞工的福利。身為白人的好處不只是在工作的物質報酬,還包括諸如「社會大眾的尊重和禮貌」、可以接觸警察和法院、擁有投票權、更好的教育,以及迎合其利益的新聞媒體。歷史上許多基於性別的類似好處都賦予男性權力,剝奪女性權力。因此現在有些人就把僅僅是談論男性需求之舉認定是攻擊婦女和女權主義,認定這樣的做法是為了保障男性所獲得的「心理工資」,讓社會回到男性在學校和工作上都享有巨大優勢的時代,或者抵制創造女性平等機會方面所獲的進步。
把談論男性視為攻擊他人,表示談論男性氣概的負面影響,比談它的正面影響安全,因為這樣比較不致於造成爭論的場面。但是對於我們希望男孩和年輕男性長大成人後的抱負,以及我們如何賦予年輕人力量,讓他們有光明的前途,卻缺乏討論。
延伸閱讀:你我可能都擁有特權,要如何善用你的特權?
他人看法如何傷害個人對自己的感受

夫妻檔蔡美兒(Amy Chua)和傑德·魯本菲爾德 ( Jed Rubenfeld)所著的《虎媽的戰甲:三項黑暗人格特質,竟然讓人出類拔萃!》(The Triple Package: How Three Unlikely Traits Exp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Groups in America)。他們書中的要點之一是,人賺錢和在學校傑出表現的能力,會受到人們對你的看法以及你對他們看法的反應所影響。簡而言之,尋求他人認可或者因不安全感而比擬他人的人,尤其有賺更多的錢或獲得更高成績的動機。
我剛到耶魯大學時,這種與外界期望的關係對我是新的觀念。先前我習慣看到的是人們對抗權威人物和當權機構對他們的看法,而不是為滿足當權者的期而努力。如果你像我一樣,在成長時期都是與恥辱感和負面刻板印象對抗,那麼這個世界只會提供有害的方式讓你衡量自己。在權威人物或主流機構的期望貶抑而非提升你的自尊心時,你不太可能會有動機要滿足權威人物的期望,或者反映主流機構的價值。
二〇〇四年發表在《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簡報》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上的一篇文章探討了他人的看法如何傷害個人對自己的感受,文中採用了一名年輕女子身體形象問題的假設例子。作者寫道:「這名女子很可能會以他人看法,來確定自己是否滿足某些標準,例如美醜和胖瘦的文化標準。這名女子或許會在閱覽服飾雜誌或與窈窕有魅力的女性一起看電視,因而意識到這些文化標準,她對自我價值的感受可能會因此暴跌。」同樣地,了解人們如何看待你或對你可能有什麼看法的學習過程,也適用於經濟和教育上的成功。
青少年輔導員的重要性

歐盟委員會指出:「青少年輔導員希望能為個人發展創造安全、支持和彈性的環境,並提供非正規教育和非正式的學習機會、個人建議、指導和支持。」《什麼是青少年輔導工作?》(What Is Youth Work?) 共同編者伯納德·戴維斯(Bernard Davies)說,青少年輔導父親員和老師或社會工作者不同,因為他們出現在許多不同的環境,與友誼團體(不僅是個人)互動,並鼓勵年輕人追求新的體驗。
青年工作者可以成為所有年輕人的有用指導人,但在接觸不屬於主流機構的年輕人方面,他們更能發揮獨特的作用。公園、籃球場、足球場、街角和巷弄之中(亦即可以找到情況最嚴重「失聯青年」 (disconnected youth)的地方)是青年工作者應該去的地方。老師不在那裡,家長也不在那裡,而如果警察去那裡,其他所有的人都會離開。青年工作者積極尋找可能沒有上學或工作,可能與警察有負面關係,及可能沒有家人支持的年輕人。對於試圖擺脫不良生活方式的年輕人,青年工作者可以帶來改變生活方式的新機會。
工作能降低犯罪機率

大多數北美社區的傳統觀念是,要讓年輕人過積極、健康的生活,工作極其重要。我參加了很多社區會議,聽到年輕人和父母尋求工作機會,以解決犯罪、上癮、家庭破裂和其他各種社會問題。來自社區的這些聲音說,只要有正經的工作,年輕人就會放棄負面行為,成為社會的積極貢獻者。
在面對危機時,北美國家的政府也對工作抱持相同的想法。比如二〇一六年整個北美的槍枝暴力事件增加,在全美三十個最大的城市,幫派暴力凶殺案數量(較二〇一五年)激增了十四%。芝加哥增加了十七.七%,居各城市之首,幾乎占全美增長總額的一半。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倫多,也增加了五十四%。 芝加哥和多倫多的政壇人物都做出了相同的回應:我們需要更多的工作。
在西方國家的城市,社群團體要求工作以保障人們更加安全,不僅是因為工作帶來的物質利益,而是就業也是賦予年輕人經濟地位,使他們與主流社會保持聯繫的一種方式。有了這種聯繫,就可以指導年輕人遠離破壞性影響,或至少可以使他們有機會找到積極的人生道路。對於在人生的其他部分都沒有正常事物的孩子來說,工作是保持人生常態的救生筏,這就是人的思想和心靈的方式,而不僅僅是為他們的口袋帶來金錢。
這些實地的觀察也得到了學術研究的支持。二〇一四年,芝加哥大學犯罪實驗室的莎拉·海勒(Sara Heller)發表了一篇文章,顯示讓一六三四名芝加哥青年以最低工資兼職的最低工資暑期工作計畫在十六個月的期間把暴力犯罪減少了四十三%。雖然減少的原因尚不確定,但海勒指出,暑期工作計畫雖減少了暴力犯罪,但未必能減少其他類型的犯罪—這表示該計畫的優勢在於社會和文化影響,而不一定來自其經濟影響。「『暑期工作計畫』只減少暴力犯罪這一事實,可能與改善自我控制、社會資訊處理和決策的作用最一致……這些都是暴力行為而非其他類型犯罪的核心。藉由針對這些技巧的課程或指導等干預措施,也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減少青少年的犯罪行為。」
工作也會對男性的福祉和家庭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其方式不僅限於收入。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的大衛.布蘭奇弗勞爾 (David G. Blanchflower) 和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安德魯·奧斯華 (Andrew J. Oswald) 在美國和英國進行了關於幸福的研究,發現失業「對男性的打擊比對女性的打擊更大」。此外他們的研究還發現「和削減收入的成本比起來,失業的成本是巨大的。」換句話說,男性的幸福感與工作相關,而非與較高的薪酬相關。
哈佛大學社會學者亞歷山德拉·基爾瓦爾德(Alexandra Killewald)對六千多名美國異性戀夫婦的研究中發現,男性失業嚴重威脅婚姻,而女性失業卻沒有這種影響。她的研究顯示:失業或未充分就業的男性,離婚的可能性較全職工作的男性高三十三%。她結論說:「當今作丈夫的因未能全職工作而不能符合養家糊口的刻板印象時,面臨較高的離婚風險。」所有收入的男性都有恆定的離婚可能,不僅是在較富裕或較貧窮的家庭中,這表示男性失業所造成的傷害並不在於所賺得的金錢,而是在於工作對男性及其家庭所象徵的尊嚴。
當社群要求以「工作」作為使年輕人積極向上的方式時,他們是在要求政治人物和商業領袖了解這些現實。它不只是關於金錢——也在於尋找歸屬之地。
後記
這本書主要的研究對象為年輕男性,作者認為若能在青少年時期進行干預,讓這些年輕人能夠有健康的討論與模範對象,可以大幅減少走歪路的機會。作者因為沒有父親做典範,教導他健康的男子氣概,他的高中時期都和朋友沉浸在好萊塢黑幫的次文化中,並為了自己的他向朋友說的崇高目標,他找了一位密友想弄一把槍,當天回家後便哭了,他知道要是真的這樣做就無法回頭了,所幸朋友後來便沒有再提,他也改變了人生目標,之後他開始尋找自己和他人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也努力幫助年輕人遠離暴力。
書中提到了許多種族歧視帶來的傷害,而社區機構和政府沒有提供必要的資源來幫助目標社區中有色人種青年,讓一個年輕人在歧視、攻擊和譴責他們的西方文化中,獨立尋求發展自己的身份、尋求安慰、知識,並在各種情況下變得激進、想要報復環境,其中也造成了警察與這些青年的互不信任的悲劇發生。
目前台灣對於新住民也仍然帶有一些歧視,2020年時,新住民二代占學生總數比例已經達到7.3%,台灣新住民、新二代人口也已經超過一百萬人,這些人也在尋找自己的身分認同,若是沒有一個社會典範,是否也會像作者身邊的人一樣,對這社會產生憤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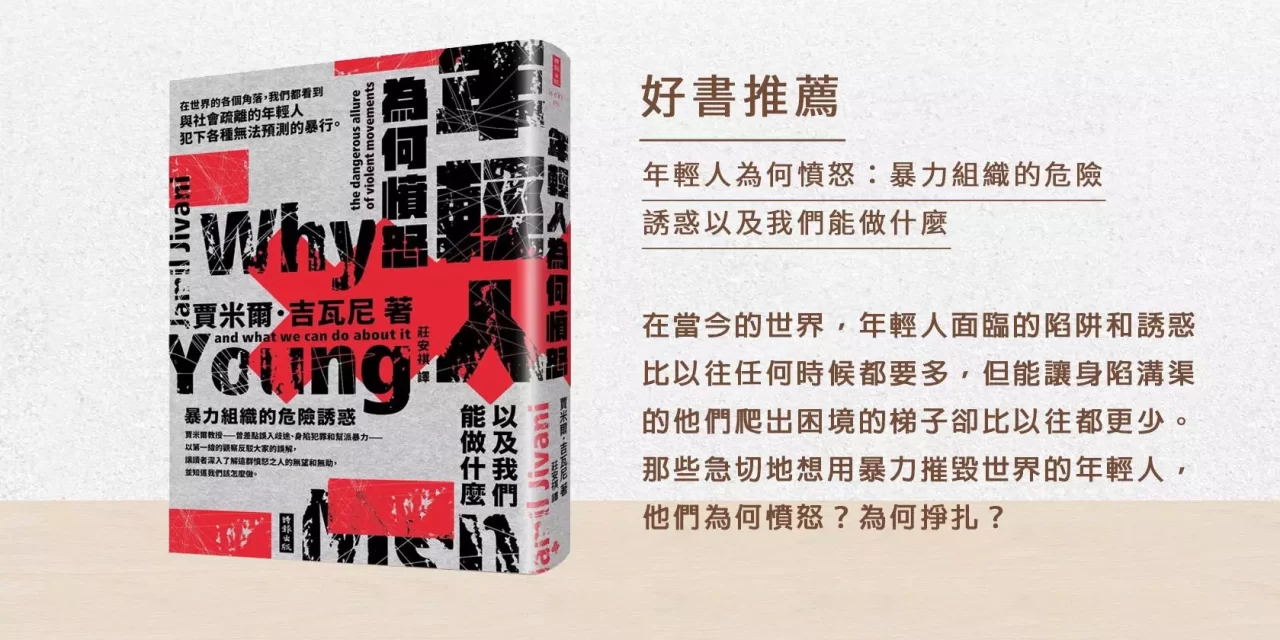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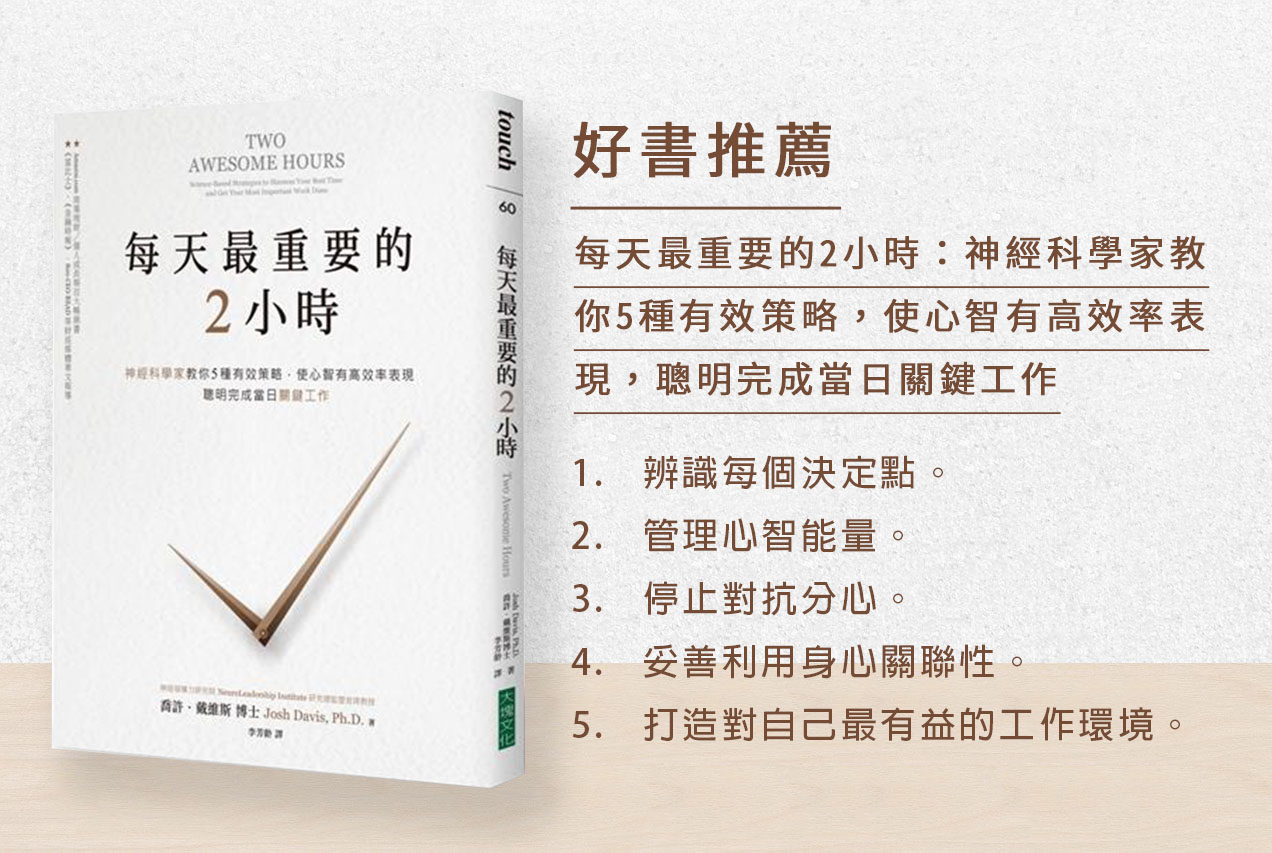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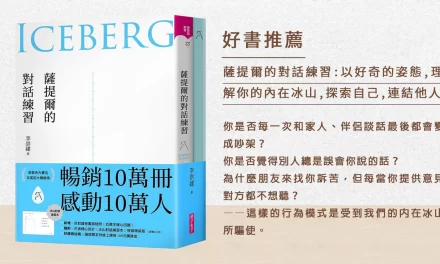


 天然水晶手鍊 藍砂石手鍊 招財手鍊 黑曜石手鍊 月光石手鍊 星空閃耀 潮酷 黑曜石 星河手鍊手串 閨蜜禮物 新年禮物,售價只要$215!立即上蝦皮購物逛逛
天然水晶手鍊 藍砂石手鍊 招財手鍊 黑曜石手鍊 月光石手鍊 星空閃耀 潮酷 黑曜石 星河手鍊手串 閨蜜禮物 新年禮物,售價只要$215!立即上蝦皮購物逛逛